批斗蔡澜体现了许多匮乏
免责声明:为了便于阅读,本站编辑在不违背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对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特此声明,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站仅作为信息展示平台,旨在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
我们新开启了更专业的知史明智PRO版本(免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https://pro.realhist.org/,如果对您有帮助请收藏并帮忙推荐,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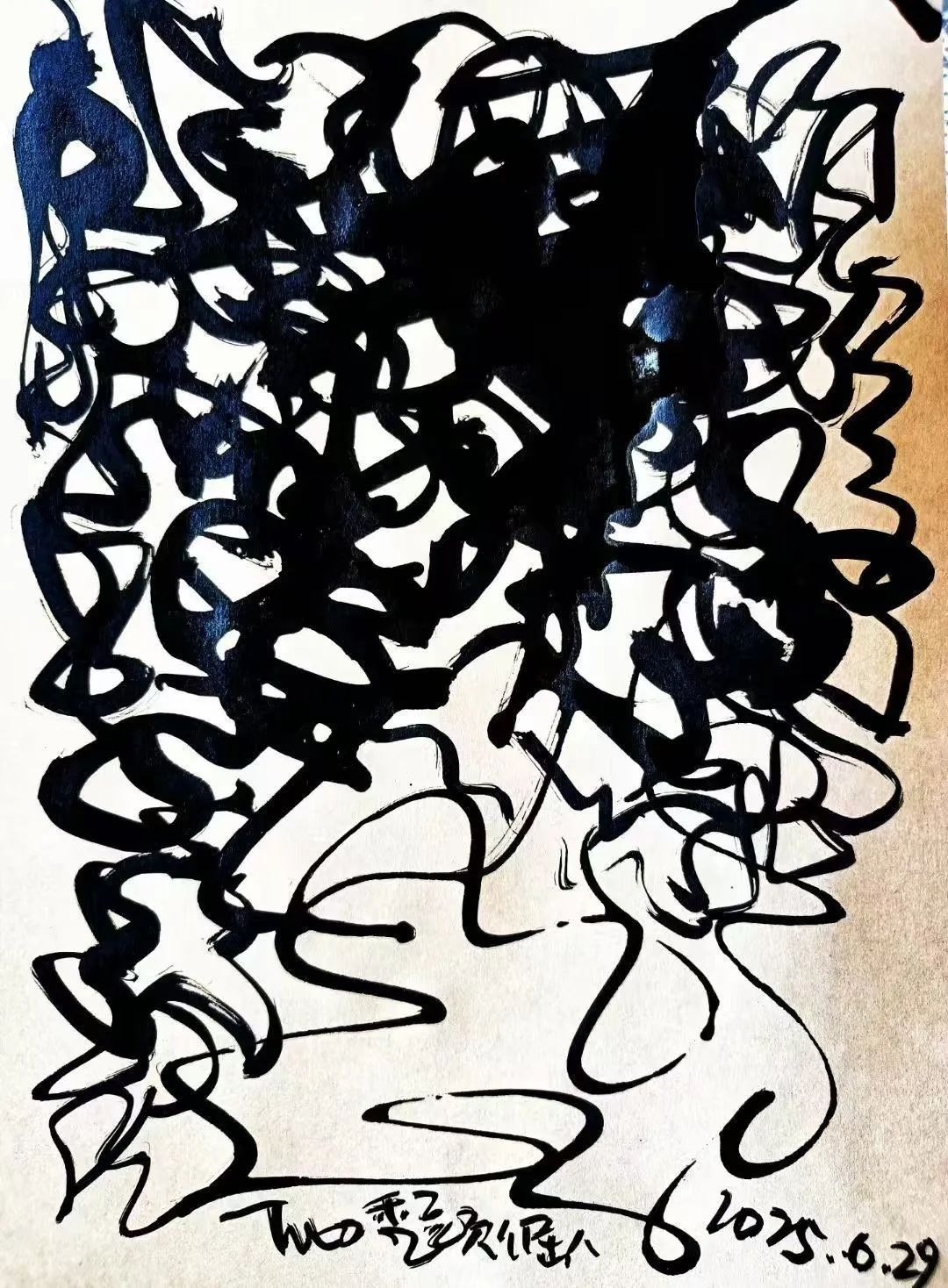
在舆论空间,人们对蔡澜的评价两极分化,这当然不是名人去世后最理想的情况,却也是常态。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死者是一类奇特的存在,他们以停歇的生命照亮生者的面貌。从这个角度看,对蔡澜的批斗揭示并见证了大陆公共讨论中许多匮乏。
我个人对蔡澜无感,他的散文随笔即使放在港中文的语境中,至多够得上中等。他早年的风流潇洒,在影视界揾食,后来靠饕餮大师名头行走大陆,仍旧属于香港叙事的回光返照,大陆人的猎奇心态最终成全了他,不足道,却也是个江湖人物。
虽然有许多称道他个性豁达,为人处世圆熟,可还是一个无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于说,他能不能成为其他人的榜样,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毕竟他从来无意成为什么样打导师。大陆人对他的许多失望,都是自身绝望的投影。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蔡澜不是一个进步人士,因为他从来没有为什么先进的思想鼓与呼。这样的看法,纯属自找没趣。蔡澜对成为别人期待的人,似乎毫无兴趣。他的享乐主义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绝对不是他。
说蔡澜是享乐主义的代表无大错,以现在的流行观念来抨击他张狂顽劣,甚或对女性不够尊重,是可以勉强成立的。但越是在做出这样的批判时,越要谨慎小心时代的分野与陆港的差别,都则很容易给他戴上一些本不属于他的游行高帽。
这种为了批斗而拼凑证据、整黑材料的情形,已经在恶评蔡澜时出现了。不出意外地,这种对名人身后论断的批斗风格,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考虑到蔡澜无有近亲属的事实,这些污蔑的人很难得到任何有效的反制,造谣成了吃绝户的恶行。
但这里不是要声讨谁,只是提醒:对蔡澜的大批斗不该仅仅看成是所有评价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流行是大陆舆论空间中诸多匮乏的集合体,乃至于是公共议论中许多病态的总和。你或许对蔡澜也不感冒,但这与沾染这些病态不该是一回事。
将陈宝莲自杀断言为“恶霸”蔡澜所为,根本上暴露出大陆网络信息存量稀少,缺乏可供检索的材料,也反映出网络用户缺乏检索习惯,为称之为“国运级”的AI搜索徒有虚名。大陆网友被海量重复的劣质信息包围,已经丧失了甄别的工具与意识。
陈宝莲跳楼自杀不过23年,可当年的大量报道已经难以搜寻,她自杀的原因其实在当年已有确认,是产后抑郁导致。至于谣传的蔡澜恶行导致她产后抑郁等,均为不实消息。可垃圾信息围困头脑,大陆人即使有检索的意识,也要突破相当强度的障碍。
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匮乏,比如新闻机构裁撤文娱报道部后,尤其在禁欲主义的媒体洁癖下,已经不能以权威信源对付造谣与传谣。对陈宝莲与蔡澜的造谣操作,走的虽是最烂的娱乐猎奇路线,却给人一种“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之既视感。
让人无语的是,谣传说陈宝莲15岁被逼拍《草灯和尚》,哪怕用大陆最烂的搜索引擎,也能找到陈宝莲出生于1973年,推算她在1992年这部电影上映拍摄前至少年满18岁。谣传者看似用恶霸蔡澜的风月事控诉她,可对陈宝莲的描写充斥下流幻想。
这些基于错误信息的捏造,或许容易澄清,可基于某些意识形态来臧否蔡澜,则需要更清醒的甄别,因为这种甄别需要非常清楚的历史意识,需要清晰的权界感,才不致于被看似有解释力的蛊惑带进沟里,这种匮乏几乎难以意识到,所以很难克服。
蔡澜生于新加坡,成就于香港,在他绝大多数生命周期内,他与现今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批斗者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只是年龄差距,阅历与意识更是天差地别。当给蔡澜定性为“压迫女性的老逼登”时,若不警惕这些次元级悬殊,就会打哪指哪。
有十几年前的女访问者,最近晒出与蔡澜合影,图说暗示蔡澜搂她腰手指很轻浮用力;可同样的照片,当年她配的是幽默文字。或许可解释为她的女性主义意识觉醒了,以今日之我更新了昨日之我的感知,可这种为了观念随意指证,与落井下石何异?
对蔡澜的批斗,将错误信息与好斗的意识形态混装在一起,形成一个看似有事实案例、有批判理论的逻辑闭环。也有少数试图填补信息鸿沟的澄清文,可按照传播理论来说等于无效,利用信息的匮乏周文深纳,在敌人的匮乏下急切鼓动,显然更有性价比。
陆港两地的民意结怨甚深,多年前的陆客在中环溺尿风波就已种下,此后随政经具体大事件持续加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建立在了解与理解之上的沟通始终难以突破。将蔡澜从他之所以成为“蔡澜”的时空中拖拽出来,就成全了类似架空剧一样的鞭尸之举。
当蔡澜被种种匮乏的阴谋阳谋包围时,哪怕批斗者竭力让姿态显得更时尚、更现代,可所用的话语又在向特殊历史致敬。所以,整体看下来,蔡澜所受到的批判,本质上是匮乏的历史循环,斗狠的不同批判者在对风月与敌人的意淫中走到了一起。
想到蔡澜一生以品鉴美食美酒为乐,尤其以寻找丰富美食的饕餮大王著称,在品类多元的享乐主义中快活逍遥。可在大陆的盖棺定论中,除了盖上一面乐天知命的旗帜,也被钉上了名唤“匮乏”的旧铁钉,这也算是他以老派身躯横跨陆港两地的报偿吧。
但凡有心者,其实不必纠缠于蔡澜是“你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人”,却可以趁机观察下成全蔡澜的年代,与当今指点蔡澜的年代有何异同。有吊客指着蔡澜的讣闻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此言不无娇嗔。假如真的存在那样的时代,丧钟是否早就敲完响完?否则,那乱人六根的匮乏从何而来?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