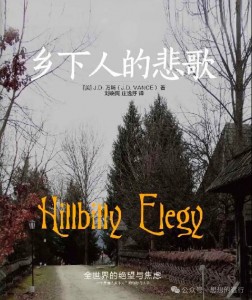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的成名,来源于他的书《Hillbilly Elegy》,中文译成《乡下人的悲歌》或《绝望者之歌-一个美国白人家族的悲剧与重生》。2013年他凭着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名气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今年又被川普选作副总统候选人。这本书记述了他在铁锈带成长时的艰辛故事和家庭心酸,与那时比起来,他这几年他可以说是时来运转,好运连绵。
这本书写得相当好,文笔流畅,能让人“一气呵成”读完。故事本身虽然也不难想象,穷白人或者说“白垃圾”的生活就那个样子,但人们还是愿意了解更多细节。句子有时很长,但是连贯易懂,我觉得甚至有点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感觉,当然后者是不断在路上行走,从东部到西部再回头,而万斯的穷白人就停留在家乡周围,对世界的变化几乎无知,只是在夫妻无休止的争吵,生孩子,嗑药,这样的事情上苟活着。
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万斯的真诚,对自己族群的困境更多是自省。虽然对同胞有很多看法,但对自己人的剖析再犀利也很难说是偏见,我看不到过去几年里他成为极端右派之后的各种极端的对其它人群的偏见。从家乡那里误打误撞进了耶鲁,这一段经历是典型的中国人所说的凤凰男经历,从凤凰男如何变成极端右派,对没有孩子的人大肆抨击,成为极右派的急先锋,这段比较复杂,我的看法是,从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他对穷白人的生活方式并不认同,也不认为全球化是让他们陷入贫困的必然原因,也因此他几年前还完全不认同川普的言论,说他本质上就是个“坏人”(Bad man),“美国希特勒”,但是,万斯是无法摆脱他的根的,就像他在书中所说,“你可以逃离肯塔基山区,但肯塔基山区不能离开你”。虽然万斯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命运的恩赐,甚至是美国及美国教育制度的爱心(可以说,如果不是照顾他的穷困背景,按照他的学业成绩,上不了耶鲁,而能进耶鲁也确实是无心之果。)既然摆脱不了故乡的穷白人思维,不如先认同吧,而且要双倍(double down)。读者在读了我下面更多的介绍会更清楚。
万斯的家庭,他愿意追溯到的,就是肯塔基东北部的山区。那里的人大都来自于爱尔兰北部的苏格兰-爱尔兰地区,这是美国乡下人的主力。我在写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系列文章中着重谈到了他们,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具有极大的反英王压迫的斗志,非常热爱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不少严重问题:落后和保守的观念,其中有些人极端散漫懒惰。英国文豪塞缪尔·约翰逊曾提到,他有一次在那里看到女人在田里劳动,男人坐在石堆旁发呆,当他问到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那个男人的妈妈说,男人不能做这些事,他们有更重要的事,但更重要的事无非就是酗酒以及帮助领主打仗。旁人这样说起他们来,是政治不正确,比如希拉里说他们deplorable,可能就是她没有胜选的原因。但是万斯自己说的也差不多:
在美国这个种族意识很强的社会中,我们的分类往往局限于人们的肤色——黑人、亚洲人和白种人,我们常说白种人有特权(white privilege)。但想了解我们的话,这个分类是不够的。我们虽是白人,但不同于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WASP)。我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Scots-Irish descent)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的一员。对这个人群而言,贫穷是传统——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奴工,然后当佃农和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又当机械工和工厂工人。在美国人的称呼中,他们是乡下人(hillbilliy)、红脖子(redneck),或者是白垃圾(white trash)。他们是我的邻居、朋友和家人。
这些人为什么与东北部的人不一样呢,实际上是继承了他们在英国时的阶级区别。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很为保守派所称道,但启蒙了的应该还是上层精英,包括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那些人。下层人民无非是在启蒙之后的环境中生存,与其说受到启蒙运动启发,不如说受到启蒙运动的冲击,而其中的一些,并不适应,于是背井离乡来到美国。那些受到启蒙运动影响成为美国建国之父以及建国之后的栋梁,大多数还是早期来自英国的那些人,包括五月花号那些寻找宗教自由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美洲的存在,苏格兰-爱尔兰人也不会来,只能在苏格兰-爱尔兰地方苟活下去,饥荒会饿死他们,就如没来的那些人一样。但来到美洲的很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另一部分没有本领,成为农民和打工族。有些后来去西部开拓,而最没有进取心的就是万斯家乡的这些白人。他们的能动性,甚至不如黑人,因为黑人还愿意到城里工作,有一定的能动性和流动性,但万斯家的这些白人是绝对想不到或者不想要这样做的,他说:
一位观察者曾记录道:“走遍美国各地,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一直令我感到震惊。他们是美国最为持久稳固、变化最少的亚文化群。当几乎到处都是对传统的全盘摒弃时,他们的家庭结构、宗教与政治,还有社会生活仍然保持不变。”
很显然,这样不思变化的族群必然是保守派。这些人,按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穷山恶水出的刁民,当然刁民也有自己的“美德”,比如忠诚、不要命、好面子,对家庭和国家的狂热奉献。
但对我们外人来说,我想提醒记住万斯的这句话:
我们也有许多不好的特性。我们不喜欢外来者或者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不管不一样的是样貌、行为或是说话的方式,而说话方式尤为重要。想要理解我的故事,你首先必须得了解,我骨子里是一名苏格兰-爱尔兰“乡下人”。
从这句话,我并不能推出他们有种族歧视的倾向,但也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美好,乡下人或红脖子对移民完全没有偏见。
关于他们的好面子,有点像中国人,万斯说他们是不愿外人看到自己恶劣的一面,在外面是不能说家里的丑事的,但很多家庭都争吵不休,常常暴力。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不付诸法律,而是自行解决,常常就是拳头。
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威胁他们的生存,上升的渠道跟他们全无关系,他们不知道有奖学金,精英学校绝不会录取他们,万斯碰巧被耶鲁大学录取,他爸爸怀疑他是否说自己是少数族裔。
因此,在偏见中他们异常悲观。万斯说:
令人吃惊的是,据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拉美裔移民当中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也落后于这些白人,但我们比他们都悲观。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这种现象就说明,肯定是金钱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确实如此,我们从未如此地脱离社会,而我们还将这种孤立感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围绕教堂,更多地依赖情绪化的修辞,而不是那种可以帮助孩子进步的必要社会支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退出了体力劳动大军,不为更好的机会而搬迁。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性带来了特有的男性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我们的男性形成了某些劣根性,难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至少在出书的时候,万斯并没有怨社会,而是诚恳地在自己族裔的身上找问题。他说: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一种解释:“J.D.,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恶化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都是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经济机会。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我拼命想相信这种观点。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但后来,我的经历告诉我: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
几年之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点钱。我在家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我的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我正需要用钱。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一小时13美元对我家乡的单身汉来说不算是小钱了——一间不错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砖公司还有稳定的加薪。干过几年的员工一小时至少能挣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这比哪怕一个家庭的贫困线都高出不少。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但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最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这里万斯对他们的散漫懒惰有具体的描述,这就是文化。曹德旺的福耀公司最近因为雇佣政策出了事,大概是给员工的工资福利违背了美国的政策。我们的内卷文化确实过分,但美国乡下白人的这种散漫是另一种极端。不仅是下层白人,白领也没有竞争力,比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场子就迟迟开不了工。也是如此。
那时,万斯也没有加入极端的右翼来攻击移民和全球化,他说:
虽然我在这本书里面关注的是我认识的这类人,即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但我并不是说我们这类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要说明白人比黑人或其他人种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摘下种族的有色眼镜,来从中感受阶层和家庭是如何对穷人造成影响的。对许多分析家来说,(尤其是华人川粉),一听到“吃福利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懒惰的黑人母亲形象。这本书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认识的一些“吃福利的”——有些还就是我的邻居,都是白人。
我当年在地砖仓库所看到的问题比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有更深的层面。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好的工作岗位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愿意丢掉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这种现象与现代美国的经济格局格格不入。
有一次我问一个相识他的爸爸做什么工作时,他说他没有工作,而且以此为荣。
我们往往总是美化自身好的方面,又对不好的方面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们会强烈反对一篇关于该地区最贫穷的人的坦诚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崇拜我们家族的男人的原因,我们在乎荣誉,也是我为什么在18岁之前假装全世界都有问题,而我们自己却没有。真相是冷酷的,但对于乡下人来说,那些最冷酷的真相,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说。毫无疑问,我们那里满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但那里也满是瘾君子。此外,我们这里的人,他有时间来生出八个孩子,却没时间来供养他们。毫无疑问,这里是美丽的,但它的美丽却被遍布乡村的环境废物和垃圾所掩盖。这里的人们勤劳,不过当然不包括那些领着食品券却对踏实工作无动于衷的人。正如我们家族的男人一样,这里是充满了矛盾。
我并不想说这些穷人就是懒惰,但他们的文化确实有问题,就是与现代经济格格不入,并不是像川普和川粉所叫嚣的,都是因为移民。这也不是我说的,而是来源于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先生的原话。我也不想再攻击万斯关于生孩子多的人应该有更多话语权的话,他在这里对孩子多,“有娘养无娘教”的情况已经给予否定。他自己的妈妈有三任丈夫,他是第二任所生。还有无数的男朋友,万斯记录下来的就有四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忘掉这一切,开始攻击没有孩子的人们。他书中的话和他后来的话对比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但没办法,他现在想开了,凤凰男好不容易可以出人头地,离世界最有权力的宝座只是一步之遥,当然要骗穷白人的选票,让极右派开心,必须睁大眼说瞎话。
对了,前几天,万斯在集会上开了个玩笑,大概是说民主党总是说他们种族歧视,他喜欢喝无糖山露饮料(Diet Mountain Dew)也可能被人称为有种族歧视倾向。结果没几个人笑,场面有些尴尬。这个典故也有出处。万斯说:
现在肆虐家乡的药物成瘾自从我妈妈成年后就一直折磨着她。而没有毒品的时候,山露汽水口腔病在那里尤甚,每个人,包括孩子,都一口烂牙,因为高糖的山露汽水。
当记者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本地人大怒,认为这是污蔑。社会学家卡罗尔·A.马克斯托勒姆、希拉·K.马歇尔)和罗宾·J.泰伦在2000年12月份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乡下人很早就学会用逃避的方式来处理令人不安的真相,或者是假装现实比真相要好。这种倾向固然能带来心理学上的柔韧性,但同时也加大了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们正视自身的难度。
对于奥巴马,万斯的家乡人听从川普的话,认为他是穆斯林,或者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不过万斯不这样,他觉得这都是家乡人的偏见。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奥巴马与他们不同:
我现在的一些朋友认为是种族主义造成了对这位总统的偏见。但很多家乡人排斥“外人”奥巴马的情绪并非出于肤色原因,而是别的。想想我高中同学中没有一个能上常春藤学校,而奥巴马上过两所常春藤名校,都表现优异。他聪明、富有,说话像个宪法学教授——事实上他就是个宪法教授。他身上没有一点像我小时候崇敬的那些人:奥巴马口齿清晰、声音动人、说话不偏不倚,不像我们这地方的人;奥巴马的履历完美得吓人;他在芝加哥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生活;他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自信,因为他深知现代美国任人唯贤的体制就是为他打造的。当然,奥巴马也曾凭借他自己的力量克服过我们许多人经历过的逆境,但那是在人们认识他很久以前。我们认为他就是与我们不一样的精英,因此他们相信对奥巴马的任何谣言。
写书的时候,万斯还很真诚,他说:
我家的情况,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我妈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瘾做斗争。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点因为学习太差而从高中辍学,也差点屈服于身边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愤怒与怨恨。现在,人们看到我时,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时,都会以为我是什么天才,认为只有特别出众的人才会走到我今天这一步。尽管我对这些人毫无恶意,但恕我直言,这种理论其实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么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
尤其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加入对移民愤怒和仇恨的队伍。他感谢很多人,包括他在耶鲁的老师、鼓励他写书的华人教授蔡美儿和他那“聪明、温和、苗条,与家乡人不同,善于沟通而不是吵架的印度妻子。
来源:白大伟 “思想的远行”公众号
作者投稿